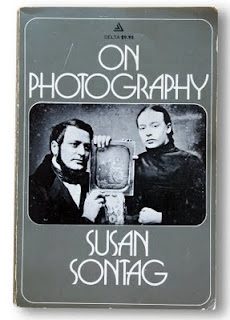Everything is so superb and breathtaking. I am creeping forward on my belly like they do in war movies...I'm sure there are limits. God knows, when the troops start advancing on you, you do approach that stricken feeling where you perfectly well can be killed.
一切是那么的令人窒息。就像战争电影内一样,我是紧贴地面匍匐前进的。。。我相信始终有极限的存在。天知道!当敌军开往你的方向的时候,那种“这可是会被杀的呀”的感觉确实会迎面而来
桑特将摄影师及作家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作家书写痛苦,因为痛楚根植于心,不吐不快,带有被迫的意境。而摄影师拍摄人事间苦难,则是带有自愿性了,因为他人之痛,本就与摄影师无关。主动搜寻各种感官上之考验来锻炼心智,是现代人的故作高深(即扮嘢),也是一种带有自虐性的行径。在资本主义国度里,桑特说,Arbus 的作品就反映出一种所谓高级艺术的偏好:去压抑、或至少减低,道德上或感官上的恶心感。但这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渐渐地我们就什么都感觉不到,结果对生活也失去反应了。
而Arbus,也唯实太过天真了。
出身大富之家的她,为了向刻板苦闷生活宣战,为了“趣味”,一头栽进了那个迷恋不幸的深渊,欲罢不能地追求那些光怪离陆、贫穷、孤寂、目光呆滞的人们,这不是应了佛家天人五衰里那句 “不乐本座,必死无疑” 吗?洋人有一个字眼来形容这种因为好奇及追求刺激而闯入社会底层的举动:Slumming。这在本质上与参加某些禁食营本就有其共通之处,美其言是让饱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学会惜福,知晓人世间幸福不是必然。但实际上你的饥饿不会为任何人带来温饱,充其量只能作为个人心志的磨练或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而已。曲终人散拔营而去之后,贫者依然三餐不续;而富者,则继续暴饮暴食。时光运转如常,个人生活依旧。荒谬之处,不言而喻。想来 Arbus 自己也深深知道,照片里的那些破碎、狂乱、不安是在暗处腐蚀着她的魂魄的。越过了界,就回不了头了。自己反倒变成了好奇心下的祭品。
Arbus 有一个本领,就是能够通过底片捕捉正常人异常的另一面。名作 Child with Toy Hand Grenade in Central Park 里头的那个金发男孩,右手紧握一个玩具手榴弹,左手则外翻呈爪状,瞪眼,嘴角横拉,在在的一幅癫模样。A Family on the Lawn One Sunday in Westchester, N.Y. 中晒日光浴的妻在艳阳下脸孔竟是如此阴冷,夫在旁掩面沉思,而孩子却在构图的后方,离开他的父母好远好远,画中暗涌澎湃,相中人各怀鬼胎。还有那一对孪生姐妹的合照,两人笑脸竟是那么诡异,看来是那么的妖气冲天,仿如魔胎降世。
这一切一切,都离开 Walt Whitman 的理想太远了。
What we have left of Whitman's discredited dream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paper ghosts and a sharp-eyed witty program of despair ~ Susan Sontag
1971年,摄影家 Diane Arbus 在服食大量巴比妥酸盐(麻醉药的一种)后,在浴室割脉自杀,终年48岁。
(Diane Arbus 本尊)